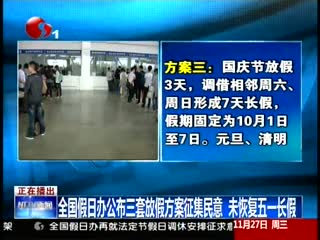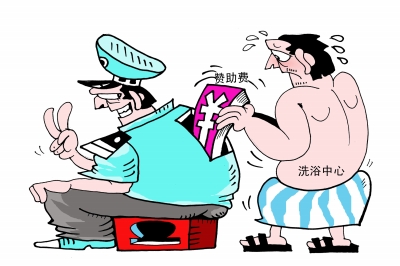就在2013年全國(guó)兩會(huì)即將落幕之際,被稱為80后洗腳妹的全國(guó)人大代表李麗,面對(duì)記者的圍追,脫口說出了一個(gè)長(zhǎng)期存在卻被忽略的現(xiàn)象——“臨時(shí)小夫妻”,引發(fā)輿論高度關(guān)注。
咋一聽上去總有些突兀甚至不合調(diào),但細(xì)想起來,反映的卻是一個(gè)極其嚴(yán)肅的社會(huì)問題,且非個(gè)別行為,而是普遍存在,用有著長(zhǎng)期打工經(jīng)歷、對(duì)之感同身受的劉麗的話說:“也許很多人聽了很意外,但是在我身邊,在我這個(gè)群體非常的常見。”
在不影響各自夫妻關(guān)系的基礎(chǔ)上,來自不同地方的他和她,組建了中國(guó)式打工潮下的臨時(shí)小夫妻。這究竟是無奈現(xiàn)實(shí)下的自然所為,還是兩情相悅下的各取所需?在此,我們并無意探討,也無心置之于道德的審判法庭,這里我們更需要的是進(jìn)一步追問:“臨時(shí)小夫妻”現(xiàn)象,真正讓誰尷尬了?
因?yàn)橹\求更好的生活而背井離鄉(xiāng),因?yàn)楸尘x鄉(xiāng)而人戶分離、家人別居——這是當(dāng)下中國(guó)式進(jìn)城農(nóng)民工的生存現(xiàn)狀。與之形成對(duì)照的,是村里的青壯年能走的幾乎全走了,剩下的基本上是“386170部隊(duì)”(指婦女、兒童、老人)在留守。捷克作家米蘭-昆德拉筆下知識(shí)階層的“生活在別處”,在某種程度上已然成為當(dāng)前中國(guó)農(nóng)民工群體的一個(gè)寫照。
可以說,在城鄉(xiāng)二元治理結(jié)構(gòu)下,計(jì)劃經(jīng)濟(jì)時(shí)代,農(nóng)民常年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,生產(chǎn)著城市所需的糧食,難得到外面的世界走一走,看看到底有多精彩;今天,2.6億農(nóng)民終于可以扔下鋤頭,跟隨市場(chǎng)經(jīng)濟(jì)大潮進(jìn)城務(wù)工,開始尋求新的生活。他們幾乎每天奔忙在車間、宿舍、食堂的三點(diǎn)一線,“常回家看看”由此成為一種奢望,每年春運(yùn)期間的“一票難求”,便是他們?cè)褟某鞘械郊亦l(xiāng)一次艱難往返的佐證,也因此他們被媒體冠以“候鳥”的別稱。“候鳥”,則意味著常年居無定所或周而往返的漂泊生活。
按照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,生理需求是人最底層的需求,也是人生存的第一需求,如果人不得不要面對(duì)非此即彼的選擇時(shí),更高層級(jí)的需求,比如社交、尊重、自我實(shí)現(xiàn)等,自然會(huì)讓位于人的生理需求。電影《老井》中,當(dāng)男女主人公被困塌方的井下,自知生還無望后,終于做了一次夫妻。被困井底的男女主人公,某種意義上不正是農(nóng)民工生存現(xiàn)狀的一個(gè)隱喻?在城鄉(xiāng)二元治理結(jié)構(gòu)下,他們中的不少人實(shí)際上已失去了夫妻長(zhǎng)相廝守的自由。
當(dāng)然,我們并無意于為之辯護(hù),在這個(gè)人性獲得空前解放和伸張的時(shí)代,任何有違夫妻相互忠誠(chéng)關(guān)系的行為都應(yīng)該受到譴責(zé)乃至法律責(zé)任追究,來維護(hù)作為人類社會(huì)文明成果之一的一夫一妻制。但如果僅僅停留在家庭倫理和群體揭秘層面的審查和獵奇,是否可能遮蔽對(duì)城鄉(xiāng)二元治理結(jié)構(gòu)的審視和檢討?我們或許因此可以滿足一下居高臨下的集體快意,卻可能由此失去了一次啟動(dòng)改革的社會(huì)契機(jī)。
“臨時(shí)小夫妻”現(xiàn)象真正讓誰尷尬了?當(dāng)然,不是農(nóng)民工群體,而是造成這個(gè)群體尷尬處境的制度。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,下決心打破二元治理結(jié)構(gòu),真正讓城鄉(xiāng)實(shí)現(xiàn)一體化發(fā)展、讓“候鳥”式農(nóng)民工不再有漂泊之憾,該是時(shí)候了。但愿,“臨時(shí)小夫妻”現(xiàn)象帶來的尷尬和刺痛能成為一次破題的契機(jī)。

 分享到人人
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
分享到QQ空間










 恭喜你,發(fā)表成功!
恭喜你,發(fā)表成功!

 !
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