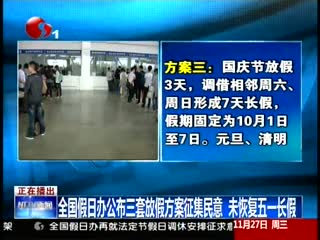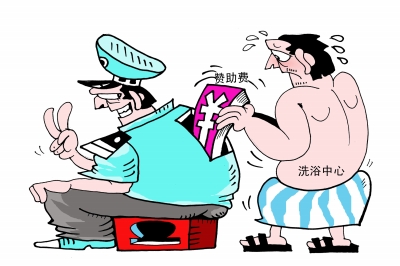對中國文化來說,通過今人的自覺,從深厚的中國文化土壤中生長出“中國新思想”,是根本之道
1937年,林語堂用英文寫了一本向西方介紹中國文化的書——《生活的藝術(shù)》。書一出版就引起轟動,持續(xù)52個星期位居美國暢銷書排行榜第一名,在美國重印40多次,被翻譯成10多種不同的文字。直到今天,我國書籍還很少在國際上出現(xiàn)過如此盛況。這種現(xiàn)象說明世界需要于中國的,是不同于他們自己原有思想的另一種思想,不同于他們慣常生活方式的另一種生活方式。
但是,百余年來,我們很少有這樣的自覺。中西文化對話中,中國面對的往往是強勢文化的灌輸和覆蓋。中國現(xiàn)代文化和當代學者在國際上也常受輕視。今天,是根本改變這種局面的時候了。對中國文化來說,通過今人的自覺,從深厚的中國文化土壤中生長出“中國新思想”,是根本之道。
當代世界深陷各種沖突之中。從軍事戰(zhàn)爭到經(jīng)濟戰(zhàn)爭,從資源爭奪到社會斗爭,從國際沖突到文化對峙,如何克服沖突、形成合作,是人類一直未能解決的最大問題。
中國先哲認為,個人無法獨立生存,人的初始狀態(tài)就是與父母和他人的關(guān)系,這首先就是一種社會合作狀態(tài)。因此,社會的基因不是個人,而是人與人的關(guān)系。所謂“禮”,就是講社會關(guān)系中的人如何存在,而非強調(diào)抽象的人。我國學者從中國文化的這個立場出發(fā),參與世界大問題的思考和討論,這種出發(fā)點已引起國際學術(shù)界重視。中國學者李澤厚在《倫理學綱要》中,更提出了中國文化的“情本體”,引起國內(nèi)外學術(shù)界對中國的“情理”與西方“理性”的討論,也引發(fā)西方文明對自身的反思。
作為歐美對外政策基礎(chǔ)的“帝國理論”,曾經(jīng)帶來三個世紀的戰(zhàn)爭災(zāi)難,已經(jīng)走到盡頭。中國哲學家趙汀陽,幾年前出版《天下體系:世界制度哲學導(dǎo)論》,描述了一個不同于帝國理論的、擁有普世正當性的中國的世界秩序模式。中國古代的“天下”,不同于西方以民族國家為主體的利益博弈模式,而是一個“至大無外”的思考單位,從“天下—國—家”這樣由大至小的方向,思考如何實現(xiàn)各個層次的和諧。
“天下體系”不承認存在著無法被理解的“絕對他者”,而相信每個他者都是這個至大無外的“天下”的組成部分,因此就排除了不可通約的、絕對的“文明的沖突”,而這種認識正是今日世界所急需的。從此,“天下體系”作為不同于長期擁有文化霸權(quán)的“帝國理論”的另一種可替代的概念和思考方式,逐漸引起世界思想界重視。當然,其中也不乏質(zhì)疑和不同意見,但毋庸置疑的是,中國學者從中國文化引發(fā)出來的新思想,已經(jīng)引起世界性的重視和討論。
面向世界的中國文化的影響,并不是按我們的主觀愿望設(shè)計制作好再端出去的一盤點心,而是在長期互動過程中,通過相互影響和雙向自由選擇逐漸形成的。中國文化面向世界,與他種文化進行對話溝通,已有悠久的歷史。18世紀以來,中國文化通過伏爾泰、萊布尼茲、榮格、白璧德、布萊希特等人吸收,包括誤讀和改寫,才真正進入西方文化主流。這是一個十分復(fù)雜的過程。
當西方學者吸收中國文化時,首先不是大量知識的掌握,而是一種靈感的共鳴,需要從各自的需要和文化處境出發(fā)。我們必須重視長期以來跨文化交流的歷史,尊重對方的處境、意愿和興趣,而不是主觀地強加于人。同時也必須看到,西方人對中國文化的一些認識,雖然本來就是真知與誤解并存,自有其片面性,但這些認識也給我們提供了嶄新的異文化視角,大大加深了我們對自己文化的認識。
在全球化的大潮中,必須看到我們所說的復(fù)興是一個五千年連綿不斷的偉大文明的復(fù)興,我們所說的發(fā)展是一個“文明型國家”的發(fā)展,這種復(fù)興和發(fā)展的深度、廣度和力度都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見的。我們有能力對世界文明作出原創(chuàng)性的貢獻,也有能力汲取其他文明的一切長處而不失去自我。這就是我們面對世界文化的根本出發(fā)點。
(作者為北京大學教授)

 分享到人人
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
分享到QQ空間










 恭喜你,發(fā)表成功!
恭喜你,發(fā)表成功!

 !
!